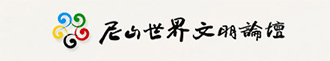身不能至,心向往之;跡雖南渡,神已北歸 朱熹為何尋芳泗水濱
2025-12-24 09:02:28 來源:大眾日報 作者:盧昱
“勝日尋芳泗水濱,無邊光景一時新。等閑識得東風面,萬紫千紅總是春。”這首《春日》是朱熹最為膾炙人口的詩作之一。
1127年靖康之變后,淮河以北盡屬金國,山東早已不在南宋版圖內(nèi)。朱熹一生居江南,足跡最北不過至建康、婺源一帶,從未逾淮。他為何能寫出如此真切如臨其境的“泗水尋芳”?
這要從朱熹自視為孔孟道統(tǒng)的繼承者尋蹤,他的精神始終“游于洙泗之間”。身不能至,心向往之;跡雖南渡,神已北歸——這正是朱熹與齊魯文脈之間深刻而動人的聯(lián)系。
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
在朱熹筆下,“泗水”并非單純地理概念,而是儒家道統(tǒng)的象征性空間。
北魏時,酈道元輾轉(zhuǎn)奔波,記錄自己發(fā)現(xiàn)泗水之源的欣喜:“水出卞縣故城東南,桃墟西北……岡之西際,便得泗水之源也……石穴吐水,五泉俱導,泉穴各徑尺余”。這里的“岡”即陪尾山,“岡之西際,便得泗水之源也”,確認泗水之源就在陪尾山西邊。“石穴吐水,五泉俱導,泉穴各徑尺余”所描述的,正是幾個由石穴噴涌而出的大泉的景象。
泗水從源頭奔涌向西,流經(jīng)的曲阜,是孔子講學、洙泗之間“弦歌不輟”的圣地。自漢代以來,“洙泗”即成為儒學發(fā)源地的代稱。
朱熹未至“泗水濱”的現(xiàn)場,卻一直在文化想象中完成精神返鄉(xiāng)。他并非在寫一次真實的春游,而是在描繪通過格物致知、體認天理后,內(nèi)心豁然開朗的境界。
朱熹由“尋”而“識”,步步深化,統(tǒng)率全詩的則在“新”字。
泗水尋芳就是到孔子那里去尋找真理,這就是詩的主題。“東風”暗喻教化,“春”暗喻孔子倡導的“仁”。這些意思如果用哲學講義式的語言寫出來,難免枯燥乏味。朱熹便把哲理融化在生動的形象中,不露說理的痕跡,這便是他的高明之處。
詩的后兩句意在啟發(fā)、引導人們認識到孔子儒學的要義,一旦這些要義廣為普及,被大家欣然接受,并取得新的認識,人們便會領(lǐng)略“聞道”的樂趣,給社會的各個方面帶來蓬勃的生機和嶄新的氣象。正如后人評論朱熹的詩作所說:“因他胸中先有許多道理,然后尋詩家言語襯托出來,此卻別是一路。”
在文化地理上,洙泗之間,還有一條沂水,也頗有地位。清乾隆間孔繼汾編纂《闕里文獻考》即確指:“洙水源在城東北五里地,名‘五泉莊’,西流入林東墻水關(guān),經(jīng)圣墓而出西墻水關(guān),又西流折而繞城西南,入于沂,以達泗。”
這條吸納了洙水的沂水,便是孔子暮春時所浴之地。正如《論語·先進》所載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風乎舞雩,詠而歸。”朱熹對這幾句的解釋是“有以見人欲盡處,天理流行,隨處充滿,無少欠缺”,乃至“胸次悠然,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,各得其所之妙,隱然自見于言外”。
四川美術(shù)學院教授李為學認為,在朱熹這里,這種天、地、人、神結(jié)構(gòu)的差異造就出來的是不同的思想世界,進而衍生出不同的審美世界和生活世界。
朱熹用“生的哲學”把人道與天道貫通,將人道之仁擴展為天道之仁,將早期儒家仁的倫理思想往深處推進。他認為,達到仁者精神境界的人,就能得到“至樂”。而這種“至樂”的獲得,不像佛教所說,到“彼岸”中去尋找,它就在我們這個現(xiàn)實的世界,即“此岸”中。
所以,朱熹特別強調(diào)在平常生活中,不斷積累道德行為,不斷去除非道德行為,以達到“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”的精神境界。這種精神境界就是理學家尋求的所謂“孔顏樂處”。
貧者士之常,惟當益堅所守
除了在思想上靠近孔孟,朱熹對山東還有另外一種情愫。他的祖先,源自山東。
朱熹字元晦,亦字仲晦,別號晦庵、晦翁、云谷老人、滄州病叟、遯翁等。在封建社會中,文人有眾多別號,并不稀奇。奇怪的是,朱熹的著述文章有許多不同的署名,或是鄒縣朱熹、婺源朱熹、新安朱熹、紫陽朱熹、丹陽朱熹、平陵朱熹、吳郡朱熹,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署名“鄒訢”。
這一現(xiàn)象使人們產(chǎn)生疑問,朱熹怎么有那么多籍貫?尤其是鄒縣、吳郡、丹陽、平陵等地,在宋代以前已經(jīng)撤置,朱熹為何將這些地方作為祖籍呢?學者詳考朱熹的家世,為他眾多的署名尋找答案。
據(jù)考證,朱熹的始祖居住于魯西南的鄒縣(今鄒城),而“訢”通“熹”。因此,朱熹化名鄒訢即鄒縣朱熹。訢為融合,《禮記·樂記》中的“天地訢合”之后,緊接一句是“陰陽相得”,可見鄒訢還有哲學的意義。
這說明,祖籍的演變,對朱熹思想的成長和發(fā)展有一定影響。戰(zhàn)國末年,朱熹的先人從山東移居江蘇徐州。兩漢時期,朱氏顯赫。東漢朱寓任青州刺史,朱氏又從今江蘇徐州以西附近徙居青州。朱氏這次返回山東青州,比原籍更靠北一些。
青州朱氏,有一支出自朱熹遠祖洪基,在東漢靈帝時,過江南遷吳郡。過江是因“國為楚所滅,乃奔吳”。另一支從朱寓的子孫開始,過江居丹陽。過江原因是漢靈帝時,朱寓“坐黨錮誅”,子孫避難丹陽,遂以為家。此后,吳郡、丹陽、平陵等都是朱熹祖先的遷移居住之地。到了唐朝天佑年間(約904年),朱熹的祖先才定居婺源。
朱熹屢署祖籍,而且還署在南宋時早已撤置的縣名,這反映了他的懷祖思想,是和他遵循孔孟之道的哲學思想緊密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。朱熹標榜自己與孔、孟同鄉(xiāng)。孔、孟及其門人也確實多為今山東曲阜、鄒城人。孔門高徒子游的故鄉(xiāng)雖不屬山東,卻是漢代的吳郡,因此又和朱熹的遠祖同鄉(xiāng)。此外,朱熹遠祖于漢代徙居,是由于當時宦官擅政,朝廷腐敗,而黨錮被誅者多為正直的讀書人和廉潔清官。這也是朱熹引以自豪的。
反觀朱熹一生,一個“貧”字貫穿始終。他在文集中每每稱窮,諸如“賤貧應(yīng)舉”“窮居奉養(yǎng)”“家貧累重”“迫于養(yǎng)親”“貧病”“窮居”“貧病日侵”“貧悴日甚”“貧病殊迫”“貧病支離”“杜門竊食,貧病不足言”“貧家舉動費力”等,言之屢屢。
《宋史·朱熹傳》說:“(熹)家故貧,簞瓢屢空,晏如也。諸生之自遠而至者,豆飯藜羹,率與之共。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,而非其道義,則一介不取也。其為學,大抵窮理以致其知,反躬以踐其實。”
在儒家的理論中,貧窮是一種生活常態(tài),并不可恥。顏回簞食壺漿,不改其樂,被后人引為千古楷模。正如朱熹回答呂侁說:“貧者士之常,惟當益堅所守,庶不墜先訓為佳耳。”
在朱熹,身貧心不貧。他身處慶元黨禁、禁毀理學的迫害形勢下,仍講學不輟,學術(shù)研究不斷,臨去世前三天,還在修改《大學》“誠意”章,真正做到鞠躬盡瘁。正如著名國學家錢穆所說:“在中國歷史上,前古有孔子,近古有朱子。曠觀全史,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。自有朱子,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學,乃重獲新生機,發(fā)揮新精神,直迄于今。”這背后的動力,是朱熹對孔孟精神的認同與追尋。他畢生致力整理、詮釋儒家經(jīng)典,尤重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。他將孔子奉為“萬世師表”,視曲阜為“道之所在”,其《四書章句集注》成為后世科舉標準,實為在思想上“重建洙泗”。
華山為虎,泰山為龍
除了對孔孟的追尋,朱熹一直關(guān)注山東。慶元元年(1195年)五月,他從汪氏處獲得《泰山秦篆譜》新本而作跋以紀其事。此《篆譜》即指傳為秦代李斯所書、刻于泰山之巔的秦篆殘跡摹本,朱熹對此類金石文字極為重視,也從側(cè)面折射出他“格物致知”的學術(shù)取向。
更為神奇的是,在地理認知方面,朱熹對泰山的山脈走勢提出了系統(tǒng)而具影響力的論述。他在《朱子語類》中曾言:“冀都是正天地中間,好個風水,山脈從云中發(fā)來,云中正高脊處。自脊以西之水,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;自脊以東之水,則東流入于海。前面一條黃河環(huán)繞,右畔是華山聳立,為虎;自華來至中,為嵩山,是為前案,遂過去為泰山,聳于左,是為龍。”
此說將泰山納入“左青龍、右白虎”的傳統(tǒng)風水格局,視泰山為中原龍脈東延之關(guān)鍵節(jié)點。這一觀點并非僅屬風水術(shù)數(shù)之談,而是融合了古代地理認知、天文方位與禮制空間秩序的綜合判斷,體現(xiàn)出朱熹試圖以理性框架整合自然與人文秩序的努力。
朱熹對泰山龍脈的論述,對后世影響深遠。清康熙皇帝在其《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》一文中開篇即引述:“古今論九州山脈,但言華山為虎,泰山為龍。”雖康熙將泰山龍脈溯源至長白山,帶有強化滿洲正統(tǒng)性的政治意涵,但其基本地理框架仍明顯承襲朱熹之說,足見朱子地理觀在官方話語中的持久權(quán)威。
此外,朱熹對山川祭祀制度亦有深刻反思。他在與門人問答中指出:“古人祭山川,只是設(shè)壇位以祭之,祭時便有,祭了便無,故不褻瀆。后世卻先立個廟貌如此,所以反致惑亂人心,倖求非望,無所不至。”該觀點直指將山川神靈人格化、廟宇化所帶來的迷信弊端,主張回歸古禮中“敬而遠之”的自然崇拜。
思想的力量,往往可以洞穿百年。明代以后,尤其清代官方對泰山祭祀逐漸去人格化、強調(diào)“祭山而非祭神”,其理念源頭可追溯至朱熹此處的批判性思考。
【編輯:董麗娜】
文章、圖片版權(quán)歸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權(quán)請聯(lián)系刪除